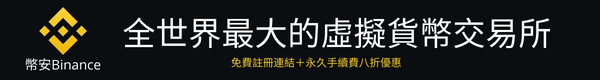今年夏天和家人去冰島旅行前,我買了一本Michael Lewis出版於2011年的“遊記”,其中記錄了他前往幾個在2008年後經歷破產和主權違約的國家的見聞,而冰島是裡面的第一個故事。但這本書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Michael Lewis在開篇序言裡寫的一個住在德州達拉斯的對沖基金交易員Kyle Bass。
Bass曾成功做空次貸危機,在賺得盆滿缽滿後,開始做空全球主權國家信貸,並透過各種方式將個人財富儲存於“硬通貨”中以應對他心中“即將到來”的法幣貶值。他做的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是實實在在地購買了價值一百萬美元的二千萬個五美分硬幣,存在達拉斯市中心的保險庫內。
在Bass買硬幣的九年後,著名金融博主JP Koning特地寫了篇文章算了算這個賭注至今勝負如何。一個五美分硬幣所含的金屬,在2011年價值6.8美分,在2019年價值4美分。對Bass來說,這筆交易到現在不僅沒賺著錢,還虧損了這些硬幣所需的儲存和保險費用。
或許交易員Bass和世界的對賭結果還未塵埃落定,但這場五美分硬幣的豪賭就像是一則寓言,故事中碳基世界裡的價值儲存物的軟價值和硬價值之間的愈發背離,讓人回味無窮。
——譯者:王想想
本文包含兩篇文章,第一篇來自於書的序言,裡面完整了講述了 Bass 的奇特故事。第二篇則來自於 JP Koning 的部落格,文章對這場五美分豪賭進行了收益分析。Enjoy Reading~如果你覺得這篇文章不錯,請幫忙分享到朋友圈~
《回形針:歐債風暴與新第三世界之旅》
Boomerang:Travels in the New Third World
by Michael Lewis
序言
寫這本書是偶然開始的,當時我正在寫另一本關於華爾街和2008年美國金融災難的書,對幾個在次貸危機中獲利頗豐的投資者產生了興趣。早在2004年,華爾街最大的投資銀行就已經創造了最終給自己帶來毀滅性創傷的工具——次級貸款的信用違約掉期衍生品(CDS),這種產品使投資者能夠對任何債券的價格進行押注,簡而言之,可以“做空”它。CDS實際上是一種保險,但有一個特別之處:買方不需要擁有被保資產。
沒有保險公司可以合法地向你出售另一個人的房屋防火保護,但在金融市場,金融家們可以出售另一個人的投資違約保險。CDS正是這樣一種產品——數以百計的投資者涉足CDS市場,因為很多人都意識到了債務推動的美國房地產繁榮是不可持續的,但只有大約十五個投資者下重注全盤押注了這一觀點。
這些人大多數在倫敦或紐約經營自己的對沖基金,低調行事,往往會避開記者。但就這個話題而言,他們出人意料地較為開放。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這些成功做空次級貸款的對沖基金經理不約而同的經歷了同一種奇怪和孤立的感覺——在一個瘋狂的世界中成為那個為數不多的理智之人,就如同獨自坐在一艘小船上,沉默地看著泰坦尼克號撞上冰山。
這其中就包括凱爾·巴斯(Kyle Bass),他經營著一家位於德克薩斯州達拉斯的對沖基金Hayman Capital。巴斯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德克薩斯人,他職業生涯的早期在貝爾斯登為華爾街公司出售債券。2006年底,他拿出了一半積蓄,又從其他人那裡籌集了5億美元,創立了他自己的對沖基金,對次級債券市場進行了大規模的賭注。
完成下注後,巴斯曾專程飛到紐約警告他的老朋友們,在很多愚蠢的賭注中成為了錯誤的一方。但這些貝爾斯登的交易員對他所說的話毫無興趣。其中一人告訴他,“你做好你自己的風險管理,我會擔心我們的。”
到2008年底,當我去達拉斯看巴斯時,次貸市場已經崩潰,貝爾斯登也已經隨之倒塌了。此時的巴斯已經很富有,甚至在投資界都小有名氣。但他的關注點已從次級貸款的崩潰中轉移。帶著上一次交易中賺來的利潤,巴斯找到了新的興趣點——主權國家的政府。
當時美國政府正在忙著解決貝爾斯登和其他華爾街銀行的次貸大規模違約問題,美聯儲用各種形式吸收了近2萬億美元的此類證券相關的風險。在此次危機中,美聯儲與其他發達國家政府作出了同樣的決策,用國債和中央銀行吸收這些由高薪金融家所創造的不良貸款。而在凱爾·巴斯看來,金融危機尚未結束,只是暫時因為人們對這些富裕的西方政府的充分信任而平息。我花了一天時間聽巴斯和他的同事們討論這可能會導致什麼結果——他們不再談論一些債券的崩潰,他們在談論整個國家的崩潰。
巴斯和他的同事們有一個新投資論點,大致如下。自2002年伊始,大多數富裕的發達國家都出現了虛假的繁榮。這些表面上的經濟增長實際上是透過人們借入他們最終無力償還的資金所推動:粗略計算,全球公共和私人債務自2002年以來增加了一倍多,從84萬億美元增加到195萬億美元。“我們在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這種債務積累。” 巴斯說。
至關重要的是,那些發放了大部分信貸的大銀行不再被視為私營企業,而是作為地方政府的延伸,從而決定了他們一定會在危機中得到救助。富裕國家的公共債務已經處於看似危險的高水平,但為了應對危機,它們仍在迅速增長。這些國家的公共債務不再是官方的公共債務。實際上,它包括銀行體系內的債務,在另一場危機中,這些債務將轉移給政府。“我們試圖搞清楚的第一件事是,”巴斯說,“這些銀行系統有多大,特別是相對於政府的財政收入。我們用了大約四個月的時間來收集資料。沒人有這些資料。”
這些數字加起來總數驚人:例如,愛爾蘭的年度赤字龐大且不斷增長,其債務累計超過其年度稅收收入的二十五倍。西班牙和法國累計的債務是其年收入的十倍以上。從歷史上看,這種政府債務水平會最終導致政府違約。“這些國家可以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巴斯說。“是他們開始實現真正的財政盈餘,但這會在猴子飛出你的屁股之後才發生。”
不過,他仍想知道他是否遺漏了一些東西。
“我想找一個人,一個非常瞭解主權違約歷史的人,”巴斯說。最終,他找到了這個領域的頂尖專家——哈佛大學的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 )教授。羅格夫教授此時正好在與他的合作學者卡門·雷音哈特(Carmen Reinhart)一起撰寫一本關於國家金融崩潰歷史的書,《這一次不一樣:八個世紀的金融愚蠢》。
“我們跟羅格夫一起過了我們蒐集的資料,”貝斯說,“他看著這些數字,然後坐回椅子上,說道,'我簡直不敢相信情況這麼嚴重。’ 我說,'等一下。你是世界上最主要的主權債務問題專家。你在普林斯頓和本·伯南克(Ben Bernanke,2006-2014年間任美聯儲主席)一起教過書,你給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美國經濟學家,在克林頓時期擔任第71任美國財政部部長)介紹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如果你不知道這個,誰會知道呢?‘ 我想,糟糕了,這世界上還有人在關注這個問題嗎?”
因此,巴斯的新投資論點如下:次貸危機更多的是症狀而非原因,導致它的更深層次的社會和經濟問題依然存在。在投資者意識到這一現實的那一刻,他們將不再認為這些大西方政府是無風險的(risk-free),並將會要求以更高的利率貸款給他們。當借款利率上升時,這些政府將進一步陷入債務深淵,導致他們借入的利率進一步上升。在一些特別嚴重的案例中 ,如希臘、愛爾蘭和日本 ,財政預算利率的上升會很快被債務利息所吞噬。“例如,”巴斯說,“如果日本現在以法國的利率借款,那麼光是利息負擔就會使政府破產。”如果金融市場意識到這一點,投資者情緒將會轉變。在投資者情緒轉變的那一刻,這些政府就會違約。(“一旦你失去了市場的信心,你就再也無法恢復了。”)這之後會發生什麼?2008年的金融危機被暫時控制住,只是因為投資者認為政府可以借到他們拯救銀行所需的一切資金。但如果投資者認為主權國家的政府不再可信了,又會發生什麼?
還有另一場更大的金融危機正等待著發生 - 巴斯確信這一點,唯一的問題是什麼時候。在2008年底,他認為希臘會是第一個發生危機的國家,並可能引發歐元崩潰。他認為這可能會在兩年內發生,但他也並不是特別確定具體的時機。“萬一需要五年而不是兩年,”他說。“萬一需要七年呢?我是應該現在就調整我的倉位,還是等到市場有一些跡象?我的答案是現在。因為當人們意識到主權違約是可能的,這筆交易就會變得昂貴。如果你等到風險小一些的時候,你就必須為這縮小的風險付費。”
我們見面時,巴斯剛剛購買了他和團隊認為最有可能違約的幾個國家的信用違約掉期(CDS)產品:希臘,愛爾蘭,義大利,瑞士,葡萄牙和西班牙。巴斯選擇了幾家最不可能破產的投行進行交易 - 高盛,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 - 但他同時也懷疑這些投行有承受一次更嚴重的危機的能力,便要求他們每天確認以保證這些交易有足夠的抵押品。
巴斯為這些違約保險支付的價格驚人地便宜。例如,希臘政府的違約保險費用為11個基點。也就是說,為價值100萬美元的希臘政府債券上違約保險,Hayman Capital只需每年支付1100美元的保費。巴斯猜測,如果希臘違約(這看起來是不可避免的),會有約70%的債務無法償還 - 也就是說每1100美元的賭注將返還70萬美元。“大多數人不相信發達國家會違約,因為我們一生中從未見過這樣的案例,”巴斯說。“並且,大多數人沒有任何理由要關注這件事。甚至我們自己的投資者也是。他們對我說,’是的,你預測對了次貸危機,但是你總是在尋找這些非常罕見的事件,所以你會認為這些事比實際上發生得更頻繁。’但我不是在主動尋找。我只是在試圖瞭解這個世界的運作方式,然後就發現了這些事情。“現在,在瞭解世界的運作方式之後,“他繼續說道,他不知道有點理智的人除了為這個更大的金融災難做準備之外,還應該做什麼。“這可能不是世界末日,”他說。“但很多人會損失很多錢。我們的目標是不要成為其中之一。”
他非常有說服力,但他的這些觀點同時也讓人難以置信。一個成天坐在德克薩斯州達拉斯的辦公室裡人,對幾乎從沒有涉足過的國家的未來作出了驚人的預測。他怎麼能知道一群他從未見過的人會怎麼樣?聽他講自己的想法讓我想起了我常常有的經歷,(我的採訪物件經常)都是那種對某種不確定事件有著完全確定的判斷的人。我腦子裡的一部分想法被他(們)的論點一掃而空,開始擔心世界即將崩潰;另一部分的我同時又懷疑他(們)可能是瘋子。“那很好,”我對他說,雖然我已經在想我需要趕的那班飛機。“但即使你是對的,一個普通人能對此做些什麼呢?”
他盯著我看,正如他剛看到世界上最愚蠢的人。
“假如你的母親問你,她應該在哪裡存錢,你怎麼說?”我問道。
“槍和金子,”他簡單地說道。
“槍和金子,”我說。所以他的確是個瘋子。
“但不是黃金期貨,”他說,完全不理會我在想什麼。“你需要實物黃金。”
他解釋說,當下一次危機爆發時,黃金期貨市場可能會受制於現貨市場,因為期貨合約的期貨合約多於現貨黃金。那些認為自己擁有黃金的人會發現他們擁有的只是幾張紙。說到這,他開啟辦公桌的抽屜,拿出了一塊巨大的金磚,然後放在桌子上。“這玩意兒我們買了很多。”
說到這,我緊張地咯咯笑著朝門口看了一眼。華爾街上的人總想讓你相信,他們能預測未來。像凱爾·巴斯這樣曾成功預測次貸危機的人會很容易相信自己也能準確判斷各種其他複雜的事情。無論如何,我當時太想要弄清楚剛剛在美國發生的事情,以至於世界其他地方會發生什麼事情,對我來說成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巴斯對美國剛剛發生的事情失去了興趣,因為他認為世界各地即將發生的事情更為重要。於是,我找藉口離開了達拉斯,並或多或少地忽視了他的觀點。當我寫上一本書(此處指Michael Lewis關於次債危機的書《大空頭》)的時候,我刪去了關於巴斯的內容。
然後金融世界再次開始變化 ,而且正如巴斯所預測的那樣。我們開始看到主權違約和國家破產。最初這個故事看起來只是關於華爾街,現在任何與華爾街在某種意義上“打過交道”的國家都成為了這個故事的參與者。那時我剛完成了關於美國次貸危機和那些從中賺了大錢的人的《大空頭》,隨即便開始前往這些“其他地方”,只是為了看看到底在發生什麼。我始終帶著一個問題:一個達拉斯的對沖基金經理到底是怎麼預料到這些奇怪的事件?
兩年半之後,在2011年夏天,我專程回到達拉斯向巴斯請教這個問題。希臘債務的CDS從11個基點上升至2300,希臘即將違約;愛爾蘭和葡萄牙需要大規模的救助;西班牙和義大利從被視為基本無風險到金融崩潰的邊緣。與此同時,日本財政部即將派代表團到美國拜訪Pimco和BlackRock等大型債券投資基金 - 看看他們是否能找到任何人願意購買五萬億美元的十年期日本政府債券。“沒有任何活著的投資者曾面對過這種情景,”巴斯說。“我們現在最大的倉位是日本和法國。如果多米諾骨牌倒下,到目前為止最糟糕的是法國。我只希望美國不會先崩潰。我所有的錢都打賭它不會。這是我最大的恐懼,對事件先後次序判斷失誤。但我確信最終的結果是什麼。”
他仍然擁有大量黃金和白金金條,其價值大致翻了一番,但他仍不斷在尋找其他儲存財富的硬通貨以對沖即將到來的法定貨幣貶值,比如,五美分鎳幣。
“五美分鎳幣中金屬的價值是六點八美分,”他說。“你知道嗎?”我並不知道。
“我剛買了價值一百萬美元的五美分鎳幣,”他說。也許感覺我無法做這道數學題,他補充道:“也就是二千萬個鎳幣。”
“你買了兩千萬個鎳幣?”
“嗯。”
“你怎麼買二千萬個鎳幣?”
“實際上,這非常困難,”他說,並解釋道他必須打電話給他的銀行並說服他們為他訂購二千萬枚鎳幣。銀行同意了,但美聯儲有了問題。“美聯儲給我的銀行打了電話,”他說。“他們問他,’你們想要這些鎳幣幹什麼?’銀行又打電話給我,問'你為什麼要這些鎳幣?’我說,'我只是喜歡鎳幣。’”
他拿出一張他的五美分鎳幣照片遞給我。在那裡,他們被堆積在達拉斯市中心一個保險庫內巨大木托盤上。
“我跟你打賭,在接下來的兩年裡,鎳幣的含量會變化,”他說。“你真的也應該打電話給你的銀行立刻購買一些。”
我認為巴斯從不是那種喜歡坐在辦公室裡盯著電腦螢幕的人。他喜歡不穩定的生活。他曾邀請我共乘他那精心改造過的福特F-250皮卡車。上面裝飾著貼紙(“上帝保佑我們的部隊,特別是我們的狙擊手”),並進行了改裝,以最大化其所有者可以擁有的樂趣:例如,他可以按下按鈕,和詹姆斯邦德一樣,在身後的路上扔下巨大的釘子。我們飛馳進德克薩斯州的山區,在那裡,用次貸危機爆發所帶來的財富,巴斯購買了一座可以稱得上堡壘的地盤:一塊四萬平方英尺的住宅,佔地數千英畝的牧場,有獨立的供水系統,以及一個裝滿自動武器、狙擊步槍、小型炸藥的武器庫。那天晚上,我們在他的美國陸軍吉普車上參觀了他的財產,並向海狸(他覺得海狸對他的水道是一種威脅)發射了配備了紅外線的最新款美國陸軍狙擊步槍。“你可以在網際網路上買到這些爆炸物,”他說,我們在黃色的山丘上徘徊,“FedEx可以運送數百磅的這些東西。”
在夜間步槍襲擊中倖存下來的少數海狸醒來會看到他們的水壩或多或少地蒸發了。
“這聽起來不像是公平的鬥爭,”我說。
“海狸是齧齒動物,”他說。
不管他在做什麼,他顯然很開心。他花了兩年半的時間觀察全球金融體系,以及這個體系內的人,最終確認了對他們不那麼正面的觀點。事實並沒有讓他失望,對這些難以理解的事情的正確判斷讓他感覺興奮。“我不是一輩子都喜歡消極的人。” 他說,“但我認為這是我們需要經歷的。這是一種贖罪,是對過去的罪孽的償還。”
再一次,一個對沖基金經理對了,而世界或多或少錯了。現在似乎是一個好時機向他提出那個困擾我兩年多的問題:在這裡,一個德克薩斯州達拉斯市的可以稱得上偏狹的對沖基金經理,一個整個成年生活都住在離這個地方几英里之內的人,不會說外語,很少出國旅行,非常愛國主義:受傷的退伍軍人是你最大的慈善事業;你幾乎不認識任何不是美國人的人。你是如何開始形成對這些遙遠國家的金融未來的看法?
“是從冰島開始的,”他說。“我一直對冰島感興趣。”
“為什麼?”
“你小時候玩Risk嗎?”他問道。“我喜歡玩Risk。我會把我所有的軍隊都放在冰島。因為你可以從那裡攻擊任何人。”
相信自己可以在遊戲裡從冰島攻擊任何人這件事讓巴斯開始學習關於冰島的一切。例如,他發現冰島被地理學家視為一個極特別的地方,能夠在長期自然災害環境中存活下來。“我們一直在說,'這些銀行破產了。’但政府一直在拯救銀行,”他說。“但就在這些事情中,冰島破產了。我想,哇,真有意思。過去一千年冰島都沒啥問題,但他們卻在克服所有這些自然災害之後,這一次怎麼能錯得這麼離譜?”
我得到了答案。巴斯的興趣始於棋盤遊戲,並以另一種棋盤遊戲結束。冰島是又一個開講(故事)的好地方。
凱爾巴斯的五美分豪賭
Kyle Bass’s big nickel bet
作者:JP Koning
本文發表於美國經濟研究所(AIER)研究員,貨幣經濟學者,金融博主JP Koning的部落格“Moneyness”
原文連結:
http://jpkoning.blogspot.com/2019/05/kyle-basss-big-nickel-bet.html
據報道,2011年,對沖基金經理凱爾·巴斯(Kyle Bass)購買了價值100萬美元的五美分鎳幣。為什麼有人想擁有2000萬枚鎳幣呢?讓我們弄清楚這筆交易的基本邏輯。
一個鎳幣面值五美分,重5克,其中75%是銅,其餘是鎳。在Bass購買他的鎳幣時,每枚硬幣的實際金屬含量價值約為6.8美分。所以Bass以5美分的價格買入6.8美分,即以100萬美元的價格買入價值136萬美元的基本金屬。
為了將這6.8美分變現,巴斯必須將銅和鎳作為金屬而不是硬幣出售。但是從每個硬幣中獲得實際金屬並不是那麼容易。自2006年以來,政府就規定擅自融化硬幣是違法的。作為受監管的對沖基金經理,巴斯應該不太願意犯法。這意味著他只能透過將它們賣給願意承擔融化硬幣風險的買家來間接變現鎳幣中金屬的價值。
在合適的價格下,肯定會有人願意購買巴斯的藏品——假設鎳和銅的價格暴漲,一個鎳幣中含有的金屬價值漲到20美分,巴斯應該很容易找到一個人為他的每個鎳幣支付12-15美分。請注意,巴斯沒有做任何非法行為,他只是以高價向陌生人出售鎳幣。鑑於他只為每個鎳支付了面值,他將會獲得超過兩倍的收益。
因此,隨著鎳和銅的價格迎來下一個牛市,巴斯將會獲益。這筆交易的巧妙之處在於沒有下行風險,因為鎳幣的價值永遠不會低於5美分的面值。實際上,和巴斯購買這些鎳幣時相比,這些金屬的價格已經下降了很多。因此鎳幣的熔化後價值也下降了,目前約為4美分,比他購買時減少了41%。但是巴斯不用擔心。他的五美分鎳幣仍然可以在美聯儲以面值兌換成美元。
這樣看來,這筆交易有巨大的上升空間並沒有下行風險 - 那為什麼不是每個人都在做這筆交易?因為這有一個問題——持幣成本。巴斯的交易還沒有得到回報,大宗商品的牛市還遲遲未到,這意味著這八年來巴斯不得不儲存2000萬枚鎳幣。但儲存東西不是免費的。以下是對此費用的估計。
Bass面臨的第一個巨大成本是倉儲。他的鎳幣佔據了很多空間。假如我們可以將鎳幣一個一個疊放,二千萬個鎳幣可以裝入一個標準的20英尺貨運集裝箱嗎?鑑於一個集裝箱尺寸為8 x 8.5 x 20英尺,它有足夠的空間容納每層32,700個鎳,高1,328個鎳,也就是43,480,000個鎳幣 - 對於Bass的收藏來說已經足夠了。
但將硬幣一個一個堆疊在一起並不是一種現實的儲存方式——考慮一下這需要的時間。儲存和處理大量硬幣的行業標準是使用一種經過認證的袋子。根據美聯儲的說法,一袋標準鎳幣的價值為200美元,即每袋4,000個鎳幣。除袋子外,銀行還常常向客戶出售裝滿價值100美元的鎳幣的盒子。無論是袋裝還是盒裝,硬幣和包裝材料之間都會有大量的“蜂窩狀”間隙。
巴斯的囤積物也會非常重,遠遠超過了單獨運輸容器的容量。二千萬個鎳重達100,000公斤,即220,462磅,而一個20英尺的集裝箱只能容納25,000公斤(55,120磅)。硬幣的重量和蜂窩狀間隙都意味著它可能需要大約4個集裝箱才能處理價值100萬美元的鎳幣。
巴斯可以找到一個願意每年以幾百美元的價格在他的田地裡儲存四個貨運集裝箱的農民,但他可能想要一些比這更正式的解決方案。一種選擇是倉庫,倉庫一般根據托盤來計價。一個托盤可以容納多達4,600磅的貨物,約417,000個鎳幣,或每個托盤104個袋子。這意味著Bass將需要儲存大約48個托盤的鎳幣。
我搜尋了一下,發現倉庫一般每月收取5到20美元的託運費。有很多變數可以影響這個數量。如果托盤是可堆疊的,佔用的面積較小,那麼月費將會減少。倉庫的位置是另一個因素,比如紐約附近的倉庫就會比德梅因附近的成本高。
鑑於Bass可以靈活地選擇一個偏僻的倉庫(他不需要每隔幾天訪問他的庫存),他應該能夠得到一個比較划算的交易。我們假設每個托盤每月5美元。48個托盤每年約為2875美元,佔其100萬美元存款總價值的0.29%。
八年多來,儲存費用達到23,000美元。減去儲存成本,Bass的100萬美元鎳幣減少到977,000美元。
巴斯可能也希望為這些硬幣的盜竊和損壞上保險。價值一百萬美元的商業財產的保險費用一般是每年約750美元。8年就是6000美元,這使得Bass的藏品價值降至971,000美元。
最後的主要成本是放棄的利息收入。巴斯沒用這100萬美元購買國債,而是將其存在倉庫中。在過去的十年裡,利率一直很低,這意味著巴斯每年的(本可獲得的)利息收入僅為0.1%至0.15%,即1500美元。因此,在2011年至2016年期間,他將放棄約9,000美元的利息,這使他的鎳價值降至962,000美元。
但在2017年,國債利率開始上升,從1%到今天的利率2%,巴斯每年放棄2萬美元投資利息為0%的鎳幣。2017年和2018年的利息成本意味著巴斯的鎳儲備已經減少至約93萬美元左右。
所以你可以看到,儘管巴斯不必擔心他的藏匿資金會遭受資金損失,但持續增長的持幣成本意味著這是一筆昂貴的交易。八年來,成本增至70,000美元,即7%。最後這筆交易可能仍然很值得。比如說,基本金屬價格上漲三倍,巴斯仍然可以在他的初始投資上賺很多錢。而且我相信他們會增加三倍,在我們誰也不知道的某一天。
我從巴斯的角度描述了這筆交易,但讓我們也從納稅人的角度來看一看。美國造幣廠和美聯儲(以及納稅人)正在為巴斯提供獲得鉅額收益的機會,同時保護他免受資本損失。在期權術語中,他們賣給他一個看跌期權。這是一個聰明的事嗎?巴斯不是一個孤立的交易,可能有很多其他人嘗試同樣的事情。所以賭注不小。
納稅人並不是在免費提供此看跌期權,其中至少有一些交換條件。在選擇持有100萬美元的五美分鎳幣時,巴斯實際上是在以零利率向政府貸款。如果巴斯選擇持有100萬美元的國庫券而不是硬幣,那麼政府將不得不每年支付2%的利息,即20,000美元。硬幣不會產生利息,所以政府不需要為他的貸款支付一分錢。我們可以將這20,000美元的利息視為納稅人為巴斯提供資本損失保護而獲得的費用或補償。
但政府是否從巴斯那裡為這筆交易收取了足夠的資金?幾年前,當利率仍為0.1%時,Bass的年利息成本僅為1000美元,Bass可能會在交易中獲得更好的收益。但是,如果利率為2%,哪一方更划算就不那麼明顯了。無論如何,政府是否應該向公民提供有損失保護的大宗商品投注機會?金融衍生品賭注難道不是高盛(們)的遊戲嗎?
政府從這些賭注中脫身的一種方法是降低鎳幣中的金屬價值。換句話說,它可以使鎳幣貶值。美國政府最後一次貶值五分硬幣是在1965年停止用銀鑄造它們的時候。
美國造幣廠可以透過改用比銅和鎳更便宜的鋼鐵造幣來進行貶值,因為鋼鐵比銅和鎳更便宜,這樣,五分硬幣對巴斯和其他投機者的吸引力要小得多——他們需要一個更大的金屬市場牛市以達到收支平衡。
或許美國可以採用塑膠硬幣,如德涅斯特河沿岸摩爾達維亞共和國。
無論我們是用鋼鐵還是塑膠,關鍵是要避免成為巴斯眼中的傻瓜。
有什麼避免成為傻瓜的更好方法嗎?五美分硬幣是貨幣汙染,我們應該直接棄用。在20世紀50年代有一枚五美分的硬幣是有意義的。20世紀50年代的五美分硬幣價值約為50美分,那是五十美分是一筆有意義的金錢。你可以在雜貨店買到五十美分的東西,比如便宜的飲料。但今天去超市,試著看看你能用五美分買到什麼。沒有任何東西。
大多數五美分鎳幣只會被使用一次。收銀員將其作為顧客的找零,然後就從那裡直接進入人們的櫥櫃,直至被遺忘。或者他們被拋入垃圾桶。或者他們被像巴斯這樣的投機者囤積起來。所有這些都是社會浪費的行為,巴斯的投機也不例外:他用來儲存鎳幣的所耗費的資源本可以得到更好地利用。
讓我們透過停止生產5美分硬幣來結束所有這些浪費。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