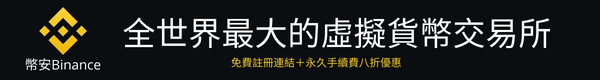6月18日,由全球社交網路巨頭Facebook主導的數字貨幣Libra測試網在GitHub開源上線,併發布白皮書。“貨幣經濟的核心是需求,往外走,才是供給,更向外,才是不可或缺的技術。貨幣的統一,在形式上,往往是外部強力下的嵌入,事實上,它依然是由需求所決定的。Libra體現了Facebook的立場選擇,也在需求、供給和技術的關係上給出了一定的答案。” 為深入思考數字貨幣並研判趨勢,浙江現代數字金融科技研究院理事長周子衡以Libra為例,對本報記者闡釋了當前數字貨幣領域所常見的四個誤區。
周子衡
誤區之一:數字社羣決定數字貨幣需求
《金融時報》記者:Face Book擁有高達27億的龐大使用者群體,其發行Libra會否轉瞬間就可以實現全球貨幣的數字化統一?
周子衡:數字貨幣是數字經濟的產物,是為滿足數字經濟需要而發生、發展的。這個看似簡單的道理,在實踐中,卻往往被扭曲,使數字貨幣成為了數字網路社羣的產物,併為其服務。如此,便將社羣活動等同於經濟活動,將數字社羣本身等同於數字經濟了;進而,社羣不論大小,均可發行數字貨幣;沒有社羣的,也可透過新設社羣來發幣。發展開來,人人皆可發幣,社羣幣蔚然成風、蔚為大觀:那些超大社羣受到追捧而謀求發行超大數字貨幣。
眾所周知,數字社羣的定位具體各不相同,有社交平臺,也有購物平臺,Amazon是網購巨無霸,螞蟻金服是數字支付巨無霸,滴滴是汽車出行巨無霸,當然還有票務巨無霸、遠端教育巨無霸,如此不一而足。但是,時至今日,不僅沒有出現無所不包的超級社羣,更沒有出現無所不包的經濟社羣。誠然,經濟社會沒出現,也不期待出現,一個全行業的數字經濟社羣巨無霸。既然各數字社羣代表以不相同的社羣活動為特色而彼此獨立,那麼,各社羣數字幣也就難以自然而然地流通到其他社羣,發展為數字通貨。因此,即便某社羣幣實現了跨國流通,但是,依然是難以實跨社羣流通。Libra安排了約百多個節點,眾多網路社羣及支付巨頭加盟,似乎跨社羣已不是問題,但是,為什麼Amazon沒有發聲,更沒有加入?是不是Libra對Amazon也實現了所謂的降維打擊呢?技術上看,一個數字社羣似乎可以無限大;現實中,它一定是有明確邊界的;邏輯上,失去了邊界的社羣,其本身也就該消逝了……
如果堅持認為,擁有27億人的超級社羣自身一定具備了神一般的力量,沒有它壓不碎的硬核,那麼,不得不說,它遠沒有看上去的那麼大,更沒有想象中的那麼硬。原因並不複雜,全球沒有任何一個經濟體系擁有27億的人口,也沒有任何一種語言為27億人所常用,更沒有一個時區的人口達到27億人……所以,這個27億純粹是統計上的簡單相加,它所成就的任一經濟場景與阿里巴巴或騰訊的相比都不在一個數量級上。打個或不恰當的比喻,直徑加總為27寸的一疊比薩餅,遠非單張直徑為27寸的大餅。單憑某一數字社羣的規模與意願,便可籌謀統一全球貨幣,這不僅僅誤讀、濫用統計數字,在事實與邏輯上,也是一個十足的偽命題。
數字貨幣是“數字通貨”,它不應受社羣的侷限。諸種社羣幣的競爭合作以及相互滲透,最終或形成一種壓倒性的數字通貨。決定各社羣幣未來走向的,不是超級社羣的體量,而是跨社羣的需求力量。
誤區之二:數字技術決定數字貨幣供給
《金融時報》記者:Face Book具有足夠先進的技術能力,Libra會不會從根本上顛覆貨幣語言與貨幣邏輯?
周子衡:只要發幣的數字技術足夠“先進”,建社羣、發貨幣,都是一蹴而就的。以至於數字經濟之有無、大小,成熟與否,都是次要的,甚或可被忽略不計了。這種認識或立場膨脹起來不得了,乃至宣稱,“沒有數字技術不能解決的理論問題,更沒有數字技術不能完成的實踐任務”,只要數字技術到位了,數字經濟便會開花結果,數字貨幣便會大行其道。“數字技術先行,以技術壓倒一切、主宰一切”發展開來, 數字技術就被塑造成主導乃至決定數字貨幣、數字經濟的根本力量。任由下去,技術語言便開始替代貨幣語言,技術邏輯也開始無視貨幣邏輯,不僅“技術第一”替代了“社羣第一”,而且技術決定供給,規劃需求。
如此膜拜技術達至信仰的“高度”,便不免淪為技術決定論者,進而,自覺不自覺地將經濟社會視作一張白紙,可以畫最新最美的貨幣圖畫。但是,經濟社會從來不是一張白紙,貨幣也從來不是“最新、最美”就最好。 數千年來,不論經濟衰敗,還是繁盛,經濟社會總是能夠找到與其相適應的——哪怕千奇百怪的——通貨形態及其制度性安排。這往往出自社會經濟本身的現實需求;離開或超出現實需求的外部設計或刻意安排,不論其貨幣構想怎樣巨集大或其通貨願景如何虔誠,終歸於失敗。從來所謂的貨幣先知,不僅在貨幣形態上如此,在貨幣數量上也一樣。在理論上,這被高度抽象為“貨幣供應是由貨幣需求所決定的內生變數”。貨幣史上的諸般變革所一再彰顯的,正是這一鐵律,亦即,需求是第一位的,供給是第二位,而技術是服務於供給的。這也正是紙幣晚於造紙術近千年的原因所在。
誤區之三:數字資產等同於數字貨幣
《金融時報》記者:作為社羣幣,Libra屬於數字資產。它和數字貨幣有怎樣的本質區別?
周子衡:社羣幣是社羣性數字資產,跨區上市交易後,成為一般性的數字資產;於是乎,受捧為可交易的“數字貨幣”,但其本質依然是數字資產,不得趨同為數字貨幣。究其原因:
首先,數字資產往往無法滿足數字貨幣的需求,兩者並無實質的交集。這同發行者的貨幣構想是否切中時弊無關,也同其貨幣願景是否巨集闊圓滿無關,根本而言,這不是由發行者的意志所決定的,而是由數字貨幣的具體而現實需求所決定的。這個“現實需求”又是什麼?簡言之,就是在什麼時間、空間範圍,滿足何種、何樣的,具體而微的,數字貨幣的零售或批發需求?生拉硬套地作出保證或牽強附會地許下巨集願,並不能瞞天過海,以資產冒充通貨。
其次,數字資產的價量不穩定是常態,不得充當計價貨幣或記賬貨幣;其流動性也差,更不能充作支付工具,而往往淪為風險資產,更有甚者墮落為割韭菜的手段或傳銷工具。比特幣——發行總量鎖定,交易價格必須涵蓋遞增的生產成本(亦即挖礦成本),然而,市場交投量和價格都無從管控調節,便出現劇烈波動;穩定幣——實行交易價格穩定的目標管控,發行量及交易量便須相應調控,這些都是名義上的數字幣,實則體現的價量關係是徹頭徹尾的數字資產的基本性狀。至於那些成功鎖定銀行法幣比價的數字支付工具,監管當局根本不認可其“數字貨幣”地位,其自身也竭力撇清,有意模糊淡化其“數字資產”的實質,以免陷入會計上的困境。
再次,數字資產發行方,在財務流程和監管合規上,無法效仿央行,實現價量穩定。具體來看,第一,初始發行量的設定及其依據何在?這將決定初始價格是否具備標杆屬性;第二,如何確定新增發行量的核定標準?它將是隨機動態、相機抉擇的,還是恆定規則的?第三,發行出售數字資產,獲得銀行法幣收入後,發行方的會計流程和記賬規則,是否能夠做到靈活、全面而自主,不受有關監管方面的強力干預?比如,發行收入的所得稅核繳,如按照出售數字資產而計的話,會計作業上就不可持續。即便發行者力圖模仿乃至複製中央銀行的會計流程作業,但是,這在公司法上就不會被認可,在財稅法上更不會被接受。
第四,如果數字資產完全背離中央銀行模式,而以去中心化的區塊鏈技術來推行其數字貨幣形態,這就意味著,數字貨幣發行是單向的——發行完成,發行方即退出,貨幣回收機制也無從發生。不安排貨幣回收,發行者與使用者之間就談不上共識機制。發行者退出貨幣共識,完全交託於使用者之間的共識,事實上,這就是一個資產的型態,絕非貨幣的型態。簡言之,資產只需要售出者,貨幣則須要回收者;只發行售出,不回收,這是資產,不是貨幣,兩相不得混同,亦無法趨同。
誤區之四:數字外匯意味著全球貨幣統一
《金融時報》記者:當前,數字經濟方興未艾,國際匯兌也面臨數字化的巨大機遇。這是否意味著主權貨幣將實現數字化統一?
周子衡:以數字技術橋接各主權貨幣,實現國際匯兌,這在技術上日臻成熟,其風險,主要有二:一方面,監管合規。其所產生的法律風險及其延伸而來的財務風險是非常高的,特別是將各主權貨幣納入到一個統一的、非銀行的數字化國際兌換體系後,區域性合規風險所產生的結構性衝擊也將是難以抵禦的。考慮到,國際匯兌監管基本上以銀行監管為基本架構,對於數字化國際匯兌的監管包容將是十分有限的,而任一區域性的監管政策調整,在時間軸上,或將頻繁發生,這就是使得國際數字化匯兌體系十分脆弱;另一方面,假使國際數字化匯兌體系十分堅挺與成功,將誘使大量銀行匯兌活動轉向數字彙兌體系,轉嫁風險並攘奪收益,這將加劇數字彙兌與銀行匯兌兩大體系之間的摩擦與衝突。無疑,數字彙兌體系的風險壓力將急劇加大,其風險管控能力面臨嚴重挑戰。數字彙兌體系意圖延緩或化解這一挑戰,將迫使它選擇並採取與銀行匯兌相接近的策略,同質化策略削弱了其競爭力。即便如此,在遭遇共同風險時,數字彙兌體系面臨的衝擊與壓力無疑將更大。
目前,全球經濟發展遠未成熟到尋求一體化甚或貨幣一體化的階段;況且經濟全球化正經受嚴峻挑戰,面臨重大調整。於此階段,以國際匯兌數字化驅動外匯數字化,尋求主權貨幣的數字化大一統,甚或建立全球單一數字貨幣體系,不是敢於超前的創新問題,而是完全脫離實際,強行推出,不僅十分脆弱,更有根本失衡的風險。
需要強調的是,Face book所將發行Libra是數字社羣幣,其優勢在跨國,但劣勢在跨社羣;它是技術先導下的數字貨幣供給,在滿足數字貨幣的具體而現實的需求方面收得很窄,在數字外匯與國際貨幣數字化統一方面放得很開;它初始為社羣性數字資產,這將極大改變Face Book自身的營收結構,但在接下來的營收會計作業上,需要更具保障性的政策安排和更具彈性的合規策略;以數字外匯作為主要戰略方向,所面臨的風險壓力和監管壓力不會少於只會更多於銀行競爭者。因此,需要更具戰略性的合作伙伴,一同逐一跳出數字貨幣的誤區甚或陷阱。